《无爱可诉》剧情介绍
无爱可诉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故事发生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之中,珍亚(玛丽安娜·斯皮瓦克 Maryana Spivak 饰)和鲍里斯(阿列克谢·罗津 Aleksey Rozin 饰)结婚多年,时间和无休无止的争吵早就磨光了两人对于彼此仅存的感情,是这个家庭走到了分裂的边缘,不仅如此,这两人都在外面找到了新的伴侣,这更加速了这个家庭消亡的进度。 珍亚和鲍里斯两人有一个12岁的儿子阿廖沙(马特威·诺维科夫 Matvey Novikov 饰),都想要投奔自由生活的两人都不愿意继承阿廖沙的抚养权,为了儿子的归属问题,夫妻两人又再度陷入了无止尽的骂战之中。就在这场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境地时,阿廖沙失踪了,作为他唯二的监护人,珍亚和鲍里斯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收起各自的武器,共同寻找这个孩子。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剧演的终章较量2重建承包人妮娜隔壁的吸血鬼美眉鬣狗之路金装律师:洛杉矶那江烟花那江雨小镇周六夜命运-冠位指定-月光/失落之室-东京爱情动作故事大师兄归还世界给你你好!梅芳草首席执行官声优广播的台前幕后007:大战皇家赌场世界新闻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咒怨杀掉那个魔术师掘密计划盗墓迷城铠真传武士骑兵僵尸肖恩良医第七季金妮与乔治娅第三季谍网追凶陪你逐风飞翔红楼梦之金玉良缘
故事发生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之中,珍亚(玛丽安娜·斯皮瓦克 Maryana Spivak 饰)和鲍里斯(阿列克谢·罗津 Aleksey Rozin 饰)结婚多年,时间和无休无止的争吵早就磨光了两人对于彼此仅存的感情,是这个家庭走到了分裂的边缘,不仅如此,这两人都在外面找到了新的伴侣,这更加速了这个家庭消亡的进度。 珍亚和鲍里斯两人有一个12岁的儿子阿廖沙(马特威·诺维科夫 Matvey Novikov 饰),都想要投奔自由生活的两人都不愿意继承阿廖沙的抚养权,为了儿子的归属问题,夫妻两人又再度陷入了无止尽的骂战之中。就在这场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境地时,阿廖沙失踪了,作为他唯二的监护人,珍亚和鲍里斯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收起各自的武器,共同寻找这个孩子。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剧演的终章较量2重建承包人妮娜隔壁的吸血鬼美眉鬣狗之路金装律师:洛杉矶那江烟花那江雨小镇周六夜命运-冠位指定-月光/失落之室-东京爱情动作故事大师兄归还世界给你你好!梅芳草首席执行官声优广播的台前幕后007:大战皇家赌场世界新闻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咒怨杀掉那个魔术师掘密计划盗墓迷城铠真传武士骑兵僵尸肖恩良医第七季金妮与乔治娅第三季谍网追凶陪你逐风飞翔红楼梦之金玉良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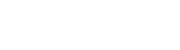
好奇害死猫。当你对特定内容抱有兴趣,说明你的潜意识就是这一类。5
好恶俗的译名,好吧这片子本身立意就不咋滴导演讲故事的能力还出奇的糟糕……原以为会聚焦于sub的肉体本能和对race play的反感间的个体挣扎,结果发现白瞎了前期一大段内心刻画,后面剧情除了猎奇有什么合理性吗?最无语的是Jaxson这个角色,为啥要给这个酱油那么多镜头,这个角色有必要存在吗?对Lee的背景和内心刻画极其马虎,让人觉得他无任何行为逻辑可言,Thomas带着锁链哼歌的那段是全片为数不多的亮点,我还以为导演会借此点题点成“爱和连接是形成/维系SM关系的基石”结果扯到最后给我来了句,“I'm just an animal and I can't control myself.”Excuse me?
前面一个小时不知所云,后面十几分钟才进入正题,本来以为会深入讨论sm主奴关系的内核,结果就讲了个故事浅尝辄止。论情色全篇没有一个完全裸露的镜头,身体和屁股都拍的很干,论剧情,故事几乎算是没有,内核也很空。看完后留下记忆点的地方:①短信交流部分用弹幕的形式,②男主带着项圈锁链在窗边唱歌的镜头,③整体色调的变化,红,黑白,蓝白。总体评价就是浪费人生的一个半小时
不知所云
TM网络高清版 虽然只有80多分钟 但还是让人无聊到觉得过了800分钟 拖沓无聊 一到男男戏就上音乐 最后草草结尾 电影不如男主的现实有意思
0 只是找不到从良的理由罢了
荒淫无度、无职业、以画同志画度日、有个黑人男朋友的黑人,终于在一次约炮中被囚禁,电击,沦为性奴。
剧情有点奇怪
还行吧,主角很倒霉,被qjf囚禁了,然后他把人杀了也没有警察找结局好像是他接受了自己的性欲,不算太保还讨论一点race play和种族歧视
就觉得很做作 但是做作的无聊
但凡你直接拍成g如v呢 探讨了个屁
口味过重……
没啥尺度,虽然满足了小朋友一点点的性幻想
乱七八糟的
不知所云!
什么啊 男友不要出去做奴
一种爱上想象中的性欲望
2024.2.8,目前4.2分。1:28:03,百度。同性恋性奴,没兴趣看完,弃了。
男主将电影搬进现实了。
其实我还挺喜欢开头那段告解:并非是镜子的不锈钢的反射下扭曲模糊的自(幻)己(想);也挺喜欢最后领带和锁链交相辉映,以及忽然抚摸过白纸的手…但是中间感觉,探究和情色都不算彻底,就有点不上不下,最后上去演讲自己的画那段的表演和台词也不是很喜欢不过这片子整体风格化还挺好的,这种片是不是不太能追求节奏?刚开始总觉得有三个主要角色是黑人但是脸盲又感觉好像只有两个,导致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和那个白人艺术家小哥。另外都违法了怎么还有人纠结SM的自愿原则…如果这片子只是为了讲人性本动物和出轨的人总有一天遇到鬼,感觉就很没意思了(不喜欢最后演讲就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