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里的刀子》剧情介绍
影片讲述在十年九旱的宁夏西海固,一个偏远的农村里,一个穆斯林老头的老伴去世了,老人和儿子举意要在老伴祭日那天宰掉陪伴老人十多年的老牛来搭救亡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老人和儿子对牛精心照料,并且也流露出对牛的不舍和对老伴的思念。在祭日的前三天,这头牛在饮它的水里看到了将要宰它的那把刀子,于是开始不吃不喝,为了以一个清洁的内里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后老人就陷入了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之中。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我的奇妙室友圣斗士星矢冥王哈迪斯冥界篇后章丫鬟大联盟你在这里原来爱上贼替身忠臣藏森林之门超时空犯罪小队灿烂阳光老千3:独眼杰克乡下人的悲歌亲爱的试用期女友彗星来的那一夜狂暴想见你父母时空使徒飞虎队世界尽头的圣骑士铁锖山之王枪神传说野蛮奶奶大战戈师奶朗·霍伯的灾难欲望都市第三季我们是演员我们与驻在先生的700日战争闭锁病房焦点女神们寻找D女郎登陆之日美国犯罪故事第三季
《清水里的刀子》长篇影评
1 ) 生不择日,死不择时——《清水里的刀子》
生不择日,死不择时——《清水里的刀子》
今天介绍中国电影《清水里的刀子》。
片名Knifein the Clear Water (2016)。
影片改编自史舒清同名小说,讲述发生在宁夏西海固的一件小事。
宁夏西海固身处内陆,有着“十年九旱”的说法,常年干旱,是大西北的不毛之地,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确定为全球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一位穆斯林老头的妻子去世。
生老病死一直是人生大事,按照穆斯林的习俗,生者要搭救亡人,为死者做一些积德行善的事情,方便死者能够离天堂更近一些。
佛教中会有烧纸等习俗,通过火焰搭建通往阴间的通道,给死者送去盘缠。
穆斯林则没有这种习俗,而是通过招待亲友、做做慈善、祈祷祝福等形式,为死者铺平前路。
老头的儿子表示,母亲收了一辈子的苦,死后要为她好好搭救,也算是尽尽孝心。
家里并不富裕,甚至算得上家徒四壁,但陪伴老人十几年的老牛年纪已经大了,准备杀了老牛,用于招待亲友。
老头思考一番后表示同意,于是一家人开始着手准备杀牛事宜,以便做好搭救亡人。
除了招待亲友,慈善、祈祷两种方式在片中也得到专门表现。
老头的弟弟因为妻子生产、家里断粮前来求助,老头准备了不少粮食送了过去,即是救济弟弟,帮助即将来到世上的新人,也是为老伴积德行善;老头多次在老伴的坟头待着,虽然无声,但他枯干的背影让人感到无比悲恸。
杀牛成了影片最大的冲突,后续故事发展中,大家都在为杀牛做准备。
虽然故事主线没有发生过偏离,但老头对老牛的不舍一直溢于言表。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老头与儿子一同照顾老牛。
好草好水伺候着,时不时还梳理梳理皮毛。
朝夕相处之间,老头睹物思人,似乎从老牛看到了昔日时光。
随着杀牛日子临近,老牛突然变得不吃不喝。
老头感到很不解,找阿訇询问原因。
阿訇就是当地宗教里的老师或者学者,是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的人,一般都被认为见多识广知识渊博。
老头认为,老牛能在喂自己的清水里看到刀子,知道自己要被宰了,所以不吃不喝。
这也就是片名《清水里的刀子》由来。
阿訇告诉老头,老牛能够感知到自己的死期,绝食是为了以一个清洁的内里,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完成最后的祭祀。
尽管已经决定杀掉老牛,但是老头心里一直无法释怀。
在动手前,老头塞给儿子一块布,要求儿子盖住老牛的眼睛,自己找拉格借口出去走走。
最后还是由儿子完成宰牛。
影片对于生死的思考已经超越故事本身。
《清水里的刀子》讲述的故事用五分钟的短片就能讲完,电影通过事无巨细的笔触将一个简单故事拉长,给观众们足够的思考时间。
生死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终极问题。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来到世上,而死亡则是可以由自己一部分做主的事情。
何时死去、何地死去、怎样死去,这些或许不能全部可控,但至少能够部分可控。
老头经历过老伴的葬礼后,也开始考虑自己的葬身之所,通过老伴和老牛的经历,总算静下来好好想想死亡的意义。
有宗教信仰的人,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给自己心理慰藉,让死者死后可以少受点罪。
影片对于生命的意义并没有给出答案。
其实生命本身并没有意义,活着的人赋予生命意义后,生命才具有相应的意义。
你如何看待生死、如何对待生命,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或许大家会想,在这么干旱贫瘠的地方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
老头的儿子却说老头离开,但老头笃定地要继续待在这里。
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很难再去适应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改变更是一件困难无比的事情。
生死这种超越人力控制的事情,是打破老习惯的最强硬措施。
随着死神降临或者新生儿落地,生命在这一瞬间完成了强制变化。
不管老人如何抗拒,都要面对这种无可避免的改变。
离开贫瘠的地方,前往富庶的地区,或许在物质生活方面能够得到改变,但对于精神层次的改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久经沧桑的人都会知道精神层面远比物质层面更加重要。
生不择日,努力活着。
死不择时,善待生命。
2 ) 一条搭救的路
电影充满了场景和场景的间隙,停顿了很久才说出话前那段停顿的空白,没说但感觉到的言语和言语外的难以体会的。
有时下一幕场景就是上一幕的注解。
最后落幕时茫茫大地雪覆盖下的大地轮廓和远处的山脊,临结尾老人点燃煤油灯念起古兰经,灭了再点,再念,再灭时已有泪光。
观片子里对话不多,其中一场是葬礼后老人去看摔断腿的姑侄儿,还掉老伴的债。
姑侄儿媳妇说起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平铺直叙地说起和老人老伴一同赶集,老伴买了很多,最后看到她买的鞋,于是借钱也去买了双。
老人回到家坐在屋子里不开灯,就捧着那双鞋坐着。
别人口中零散提起的老人老伴就是"苦了一辈子了",别的再没有,这些可能是老伴唯一表现出自我愿望的一次,老人抱着它,想些什么呢。
另一段对话是老人和儿子,说起外出打工。
老人不同意,庄稼里的洋芋和井里放的水就是他依赖的,出去危险;儿子觉得有可能明年收成不好水也吃完了,出去打工也不累,危险哪里都会有。
隔壁要生娃婆娘的老头过来了,问起老人老伴的事儿办得怎么样,吃面也是劝几劝吃了半碗,再要加就不吃了。
老人问你不常来有什么话要说么,老头没说话,老人出去喂牛了,老头跟着出去,说出自己来是借米给婆娘吃,老人顿了顿,走去厨房让媳妇给了他半袋米。
之后背着米的老头在暗下来的大地上走回家,再之后要生娃时候老人,媳妇,阿訇走在夜里的大地上,人好像化成大地的脊背,担起这些。
还有几段片段是阿訇念经,给亡人,给新生的婴儿,最后给牛。
这个阶段性的生命仪式在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是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引路,以至最后老人希望为自己渡过这个心理难关也在念古兰经。
牛牛在决定被宰之后,先是老人的儿子给牛刷身上,然后给牛割苜蓿,老人在雪中带牛出去,给牛铲土垫窝,最后一次带牛出去在满天遍野吃草,再后来,牛开始不吃不喝,老人故意在宰牛的那一天出去转悠,避开这一幕,出门前塞给儿子一块布,应该是后来捂牛眼的那块布。
人老人最开始不愿意宰牛,说是没有犁地的了,其实通过牛看自己。
在儿子劝说后,老人一直在想这个事儿,给自己洗了个澡,然后给自己洗了个小净,再然后在看到牛不吃不喝后,去找一个老人家说话,说到牛是大牲,想起原先老人们说牛在被宰前几天可以看到水里的影子,老人家回话,牛不吃不喝内里清洁,高贵的。
老人觉得自己,人,反而两眼一抹黑,什么都看不到,老人家回道,人也贵,各有各的活法。
真主的奥妙,参不透。
牛和人有一处镜头是老人儿子洗牛,牛背对着镜头,露出清晰的肚子下垂,脊梁高挑的轮廓;背后的老人也看向牛,背对着镜头,人牛的背影这一画面让人觉得老人也在看向自己,尤其总是说道牛娃子之前也挨了不少他的打。
另一处是发现牛不吃不喝后,老人把牛牵出来,新打了一盆水,牛依然不喝,老人看向水盆里,映出牛和老人,老人叨念着真是不吃不喝啊…然后回到屋里,和老牛透过窗户相互看着。
四十这天的搭救终于在结尾到达,作为举意,牛被宰,老人老伴苦的一生被搭救;老人想看到的眼前事没有映在水面上,但确实透过牛,透过姑侄儿一家,生孩子的一家铺就了路,那本古兰经念了又念,不是为了释然或者搭救,而更像是看到老牛生前选择后一种内心平衡的找寻,老人没法像老牛,也许他的"贵法儿"就是完成搭救他人的过程吧。
片子好像不是在讨论清洁,虽然这确实是呈现的方式,而是在讨论"贵",一种超越一种live otherworly。
不过人到底不如牛本体,后者在自身之内就完成了,前者还是要靠他人或者越过自己而达成。
3 ) 静止的清水
文|汤旅 发表于MOViE木卫王学博的这部《清水里的刀子》两年前就在上海有点映了,那时因事错过了,因此一直把这个遗憾留到最近——它正式上映的时候。
没有想到一部文艺片拖了两年才能在大银幕上看到。
这部影片曾获得了第21届釜山电影节的新浪潮奖,在银幕上,它的独特之处得以最好的呈现。
在中国,偏远农村的题材很容易处理成画面粗糙的现实主义,重点在人物矛盾与命运,但这部影片回避了起伏的情节,似乎类仿阿巴斯对生命的思考,将剧本对话、故事情节全部精简化,只留下老人日常所做之事、独处的所思之时。
在丢弃常规的剧本后,导演请了耿军的御用摄影师王维华,给它在所呈现的影像上推向极致。
每一个画面、人物调度,都极为精细,于是它脱离了惯常的现实主义风格,而产生出一种疏离日常的油画风格。
绘画呈现的是可见之物,在绘画中,画家往往会隐去自己不想呈现的部分。
在《清水里的刀子》中,老人缓慢行走在小平房前,净白的墙面使画面干净整洁,除了一些零星点缀的枯枝,画面内没有其他现实主义电影里常见的杂物。
因此,这部影片可以说与现实主义背道而驰,从而呈现了趋近油画的风格。
片中有关宗教的表达很多都依赖于这样绘画般的影像,用视觉直接言说宗教的林林总总。
在影片开头,几个农民在荒地里耕作,有意安排的人物动作和位置关系构成了静态绘画,很容易想起米勒的《拾穗者》。
在老伴去世时,众人做祷告,在幽暗的低调光下,众人围坐在一起,进行着仪式一般的活动,回归到了西方古典画派的风格上、群像、宗教、静观的动作;我们所看到的老人“洗澡”,其实是穆斯林的“净身”(大小净),是一种宗教行为。
在净身中,老人正对昏暗暖黄的墙壁,导演仍然把场景精细布置,去掉杂质,画面中只有后景墙壁、前景净身的工具和老人瘦削、线条分明的身体。
处处体现着明暗对比法,这种肌体的呈现在德里克贾曼《卡拉瓦乔》中也是如此。
贾曼的《卡拉瓦乔》正是因为这样的鲜明的有意安排感,影片伊始就给观众疏远的陌生感——我是一部精美的艺术作品,而不是贴近生活的电影。
穷苦的环境并没有给观众熟悉的现实主义电影的生活感,而像是本身就保持了距离的戏剧。
伤者居画面左下、女人和老人分别占据画面的左右分割线,墙上报纸的贴放整齐有序,墙壁虽破旧、脏,但在有意的布置下反而与整体形成一种干净简洁的感觉。
即便是素人演员,在这样的有意安排下,方言和自然生活也开始失效,于是他形成了另一种不同于非职业纪实派的演员气质。
在映后访谈中,导演说到有许多业内评委对老人的评价是:他长了一张非常电影的面孔。
在我看来,沉稳、皱纹,甚至是瘦削极有线条感的肌体,都符合西方古典绘画的美学要求,在摄影中,则十分接近现实主义摄影的特质。
摄影之所以不同于电影,在于它的静止感。
在传统的人文摄影中,构图、人物关系、光线等都极具考究,也就是说,它捕捉到的并非自然的现实,而是摄影师有意通过景框塑造出的极具张力、内容的现实。
所有的事件、主题、符合都浓缩在这一张图中了,因此要求画面极具表现力。
而电影,一种流动的影像形式,它不需要每一个画面都那么精炼,时时刻刻都被处理地完美无瑕,它的叙事随着流动而变化,主题符号则被拆解游离在不同的画面中。
于此,《清水里的刀子》则更像是传统观念里的人文摄影艺术,而非流动的电影。
在大远景的清蓝色的雾霭中,人物与生命之树、远山构成了极像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的影像,但不同于那些的是,《清水里的刀子》几乎不进行镜头的行云流水的调动——它是静止的。
当我们期待每一个精美的画面能有所运动时,它就被剪辑到另一个画面了。
因为影片是由不同的精美的画面剪辑而成的,而恰好,这些精美的画面又极具符号仪式感,每个画面都有自己饱满的符号表达。
视觉足以让人振聋发聩,台词的隐蔽留给了视觉足够的阐释空间。
因此它绝不是对欧洲艺术大师的模仿,它是静止的;同时也并非是对侯孝贤等人固定镜头生活态电影的风格呼应,它的极具仪式感的构图摄影抛弃了现实。
它形成了与自然感知类型的影片截然不同的风格——一个精美的、静止的艺术品,而非简单的对现实描摹。
在声音处理中,它保持着和视觉一样的精美极简的处理方式。
不同于自然感知的影片(《天地悠悠》、《沼泽》),它隐去了艺术品中非必要的声音,隐去了自然环境中该有的嘈杂音,只剩下时钟的滴答声、倒水声、柴火燃烧的声效、牛在环境中的零星声响等诸如此类的细节声。
这同样有助于完成这样一部看上去现实,实际上疏远的艺术品。
同时声音元素也并没有被放大,这更有利于加强视觉的重心。
清水是流动的,而刀子确是静止的。
牛知道自己将被宰割的宿命,磨刀与否则无关紧要了。
4 ) 向死而生,性高洁
说实话,没太看懂。
不是很懂他们的信仰,习俗和仪式。
不理解但是尊重。
很喜欢整部片子的摄影。
从海报就能看出来,设计感强烈,色彩搭配巧妙,这种色调能渲染烘托压抑沉重的氛围,影片里也充满了摄影美学,都是这种冷色调,阴冷沉重,但是视觉上很舒服,不同于水形物语的那种有点浪漫暧昧孤独的蓝绿色,这部色调只单纯的孤独深沉。
这也正好契合了主题吧,对生与死的思考。
整部片子都能听到时钟的嘀嗒声,就像生命,一秒一秒的在流逝。
印象很深的一个镜头是,下雨了,小孩子立马回屋拿桶来接水,然后家家户户都跑出来接水。
西北地区有多缺水大概能想象到了。
老头洗澡的镜头也很震撼,一小桶水,拔掉木塞,没有肥皂,没有沐浴液,就那样用力地搓着。
看着似乎很平淡,但却有种强烈的仪式感。
还有就是有段台词说人不如牛,牛会保持自己的高洁。
恩,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思考是好的,不要以为人是万物之灵,自大狂妄,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
不过得承认,很多时候,有些地方,人确实比不上牲畜。
想起那句话,我见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
有很多人确实还没动物那样重情重义,性高洁。
记得牛在印度是很神圣的,被当做高洁的圣物,有很高的地位,牛可以随意的在路上走,所有的车子都要避让它。
王小波的散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也说了插队时喂养过一头猪,和别的不一样,这只猪不甘命运的安排,敢于挑战反抗。
生死是个永远的哲学问题,我还没参透,不敢多说也不能多说。
而关于人是否比动物高级,我觉得作为一个人,还是谦虚点好。
对待生死,我觉得还是淡然点坦然点好,活的时候好好活,死的时候平静的死。
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
活着是在路上的死亡,而死亡是活过的生命。
也许人生就是一场虚幻的梦,你以为死亡是结束,其实是新生。
5 ) 《清水里的刀子》:复现生活的“静物电影”
从学生时代的短片习作到十年之后的长片处女作,导演王学博对《清水里的刀子》情有独钟,在对同一个故事的揣摩、雕琢与反复讲述中,完成了自己对电影的朝圣。
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改编,在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并不鲜见。
以王朔小说《顽主》为例,这个带有乌托邦理想的喜剧故事在不到三十年代时间里被讲述了三次,从《顽主》(米家山,1989)、《甲方乙方》(冯小刚,1997)到《私人订制》(冯小刚,2013),跨越了80年代、90年代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新世纪十年。
但王学博对《清水里的刀子》的反复讲述却是另外一种。
如果说《顽主》的三次改编恰好记述了改革开放所开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相互叠加的立体变迁,是对“变化”的一种历史观察,那么王学博对《清水里的刀子》的反复讲述则是对文本深度的大力挖掘,是对“不变”的一种内在自省。
《清水里的刀子》改编自石舒清的同名短篇小说。
回族老人马子善的老伴亡故,儿子耶尔古拜为了在四十日祭那天虔诚且体面地让母亲得到搭救,提议杀掉家里唯一的一头老牛。
老人既不忍杀牛,也不忍拒绝儿子的孝心,只得无言默许。
在余下的日子里,耶尔古拜精心地伺候老牛,但老牛却在祭日前三天忽然开始绝食。
马子善想起了老人们的传说,牛在献出自己的生命之前,会在饮水里看见与自己有关的那把刀子,自此便不吃不喝,然后清洁地归去。
祭日前夜,马子善在牛棚里陪了老牛一夜,出了牛棚又将宰牛祭祀一事全权交给儿子,自己径自出门去。
黄昏才归来的他看见院子里放着硕大的牛头,他感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张颜面如生的死者的脸”。
导演要反复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带有民间传说色彩的简单故事,电影的改编也不过是在死亡和祭祀之外填上了西海固大地上的生死轮回。
从短片到长片的两次不同讲述,也是从剧情片到作者电影的重要转变,极其稀疏的对白和极为松散的剧情让叙事链上的“宰牛”变得松动,甚至变得不重要。
在贝拉·塔尔式的镜头里,重要的是生活的节奏和本质。
笃信宗教的徘徊在贫困边缘的回民们,在大量固定镜头和长镜头中复现了无言的大地和无言的生活。
正是这种无言的“复现”让我着迷,在这里农村仅仅是作为生活的农村,而不再是作为想象载体和乡村寓言的农村。
也因此,这部名为“清水里的刀子”的电影,并没有那样一把真正的水中刀,传说仅仅只是传说。
尽管这是一部迷人的复现生活的“静物电影”,但用4:3的画幅来拍广阔的西海固也还是会被质疑,为什么要把这片荒凉辽阔的土地锁闭在狭小的画幅里,而不在视觉冲击上再造一个当代《黄土地》(陈凯歌,1984)?
但答案或许恰恰就在“局促”的画幅里。
在《黄土地》里,“黄土地”虽是顾青眼中质朴纯真的乡土风情,但也是翠巧心中沉重无边的牢笼枷锁,这片荒凉的土地最终既留不住顾青,也留不住翠巧,仿佛在讲述着无言的“死”。
而在《清水里的刀子》里,西海固的“青土地”不再担负讲述东方寓言的重任,春夏秋冬、雨雪风霜、生老病死试图讲述的是大地上无言的“生”。
把辽阔的西海固锁定在4:3的画幅里,意味着这将是一个少有的“等比例”的故事——无论大地如何辽阔,地上的人们终究只踏一方。
除了4:3的画幅,复现还表现在情感的节制上。
整部电影没有配乐,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放弃了煽情和感染,只将情感寄托于画面,而稀疏的对话和大量的固定镜头又将共情的可能一再打破。
最后只剩下青灰色的大地和土黄色的回民,犹如一幅幅精致的油画。
这便是“等比例”的另一重意义,在这片大地上,人们的生活贫困但不可怜,虔诚但不愚昧,生活中的事虽然微小但很重要。
换句话说,之所以显得情节松散,并不是无力叙事,而是极力回避编织逻辑严密的故事链,生活自有其平淡无奇的一面。
《清水里的刀子》给我带来的奇妙观影体验也在于此,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真正做到平视农村的电影。
在电影中,平视具体地表现为注视,大地、回民、动物在长镜头里融为一体。
正因为谁也离不开谁,宰牛一事才显得纠结,既不忍又不得不;也正因为人有纠结,所以牛对死亡的先知才让人震惊。
马子善老人内心的落寞、酸楚与悲痛几乎不通过语言来表达,他只是长久地注视着眼前的生活,而我们注视着他。
这种注视让人想到另一部纪录片《二十二》(郭柯,2017),如果说《二十二》对当下生活的探寻(区别于对沉重历史的追问)是一种“深情凝视”,那么《清水里的刀子》对生活的复现(区别于对乡村故事的精巧编织)则是一种“平静注视”。
透过眼前的镜框,透过西海固大地与回民,观众将经历一次来自他乡的缓慢追问,生命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
意义又是什么?
电影中马子善老人的每一次低头都让我印象深刻:老人在坟院前一步三顿地驻足回望;老人在炕上背对着儿子聆听宰牛的建议;老人握着亡妻的鞋子回想过往;老人在雪中牧牛;老人在牛棚昏黄的灯光前听弟弟讲述无米可炊的窘境,一言不发转身看牛;老人在油灯下读经,黝黑的眼睛里泛着点点光。
景中无言,画里有声,或许正是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
(本文已发表于《新华网》)选择这样一个故事,用这样一种零度叙事的方式来完成一部电影处女作,在新导演中是少见的。
对画面的精致雕琢一方面展现了导演对电影的虔诚,另一方面也暗藏危机,不讲故事如何证明自己会讲故事?
“静物电影”到底是偶一为之的策略,还是导演着力追求的风格,答案恐怕只有留待下部作品了。
6 ) 与孤独和平共处
一部关于穆斯林民族的电影。
现在藏地很火,讲述藏族同胞的电影也越来越多,还有更多不少藏族导演,基本上都能打上文艺的烙印,这一切于他们的生活,都成了我们眼看的某种标签行为和艺术。
关于伊斯兰教,同样三大宗教之一,因为信仰的民族多人数广反而很少有文学作品(也有可能我书读的少),这部电影,从穆斯林民族宗教风俗切入核心的情感——关于亲情,死亡,生命,孤独。
其实还是探讨了生命的终极,加上了宗教,含义更为复杂。
老伴去世(无常),儿子媳妇各自的态度,媳妇带起了头巾,儿子想给苦了一辈子母亲宰大牲,体面的走,只有老父亲,一块心头的肉剜去了,悲痛是有,每每到坟头沉思陪伴,失去了一个人而不是面子和符号。
对于要被宰杀的老牛,同样都是陪伴,老伴被动的离世,而牛要主动被送走,知道离开的确切时间,矛盾的情感也随之扩大化,理智上宰大牲为了家里人和老伴好,况且牛已经很老犁地也不能几年了,情感上,一次又一次的离别实在痛苦,老人在这种情境下越发沉默,连儿子也要外出打工。
孤独大概是人最需要学习的情感,苍老沟壑的脸上,眼神晦暗不明,和黑暗融为一体,几乎和世界隔绝,安拉能否告知答案?
孤独?
生命?
平凡的人要怎么与生老病死和谐共处?
电影很安静,拍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清晨和傍晚,映照出生和死亡,很多镜头,没有什么言语,大部分是老人孤独的侧影,陪着牛,坐在坟边,走在路上,其中有两段镜头外的对话,一个是和村委商量圈坟地,被驳回,一个是和阿訇寻求答案,牛为什么在临死前不吃也不喝了,没有答案也不被关注。
这两个镜头中,一个隔了烟囱,一个隔着门,现实也好,信仰也好,给不了答案和安慰。
孤寂得无以复加,就像鸣响的水壶,情绪几乎要炸裂,又被按压下去,销声匿迹于此。
7 ) 这盘清水照见我心里装满刀子
对回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和信仰的认识,一直都是道听途说的,直到这天我走进广州“光塔”怀圣寺,才知道那几乎都有我自己的误解。
光塔|广州|2009.11.25那天是我第一次走进回教庙宇。
怀圣寺很安静,只见到几个工作人员,我也不好乱问,也不敢乱走。
见有些小册子,就选了几本感兴趣的回家看,一下子就记住了其中的这句话:“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小册子上说,接受这句话的人即是穆斯林。
我想我那天就全然接受了这句话,否则不会只看一眼,至今还记得。
这大概与我之前遇到不少“巧合”的事情有关,接二连三的,我就不再觉得是巧合了。
祂似乎在暗示我有一个更大的存在。
好奇的我去请教高人,读了一些经典,然后就是重温了一遍曾经学过的《电子学》。
行为怪异的电子一入教科书,就让当年的我认为理所当然而无视其怪异。
这时才发现,电子怪异行为所引出的量子物理学有此一说:这个宇宙,只不过是某个更大的存在的一个局部。
起码在这点上,科学与古老的各派宗教不再有冲突。
在这个科学框架下,或者说是我们当下的宿命,不甘心受困于局部的人,看来也只能够找个信得过的过来人,然后跟他(她)走就是了。
不过信谁?
就剩这么一个最简单的大问题。
这样的活人能遇见,不知概率是多么的小?
万幸的是,这样的故人,谁都能亲近。
能给我提供参考的,其一是电影。
电影《清水里的刀子》(2018)将回族同胞面对生老病死的态度,浓缩在一个“由杀牛而引发的一连串生活琐碎故事”之中,让我只用一部戏的时间,就大概了解到一些他们的信仰问题。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也能用这盘“清水”,照一照自己心里装满的那些“刀子”。
2018.9.30 http://william-ho.lofter.com/post/6c3aa_12af8dc2a
8 ) 我看清水里的刀子
看的电影,在此寥发表一下见解。
从艺术角度看,全片氛围很塑造的干净利落,有很返璞归真,不管是从演员表演很到位,很真实。
故事叙述略显导演功底不足,镜头设置也不是很合适。
整个片子的环境需要有生长经历的人看可能更有感觉,西部广大贫困地区,有信仰基础的群众看或许跟能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和生活与宗教的融合。
故事内涵表达不到位,但作为小众电影,也算是不错了,一星给与鼓励。
希望能出更多的反应民生的片子。
9 ) 无差别的宿命论
主创见面会这种东西大概是专门用来将导演拉下心中神坛的;为保住对电影和团队的敬意昨晚提前离开,现补交一篇影评。
《刀子》中呈现的所有人类学奇观几乎都与水有关,后者古典画意的表达承接着我们一直以来对穆斯林的意淫;“清水中的刀子”一言蔽大概是:寿终寡欲之时面对宿命的状态——然而他们并不会因为阿訇的告诫就摆脱惶惑;信奉终身的净身教义,物质生活的淡泊自给——这些我们原本以为能够对抗死亡恐惧的武器,现在依然无法施予绝对的镇定。
所以大概,死亡与民族无关,终究是人类共同的宿命悲伤。
10 ) 依旧符号化的少数民族
首映导演(左)交流影片放完,我特别特别想问导演一个问题:马子善老人家里,究竟有几个人?
这个问题很简单。
朋友说我这是纪录片式的问法,但是当导演这么费尽心机用油画般的摄影和静谧的色调拍了一部表现“回族文化”的“回族电影”,我实在很难不用纪录片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在影片开始的地方,马子善的儿媳妇和另一个女人在厨房里忙碌,一个显然年纪比儿媳妇要大一些的女人。
影片中段,马子善老人问儿子:“你今年打工怎样?
”我一愣,儿子都已经在家这么久了,怎么突然问这话?
这使我作出了逻辑判断,他大概有两个儿子。
但是直到影片结束,我也没有能够确认,他到底是有两个儿子,家里两个儿媳妇,还是他续了一个弦。
又或者,这是西海固地区回族传统里有时候会有“小老婆”的隐晦展示(当然有两房妻子的大多是富裕人家,回族很强调对女性的“赡养义务”。
以片子里老人的家庭情况看,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影片再也没有镜头来交代这些人物,好像把他们就忘掉了。
导演在西海固生活了十个月,作为一个城市人,他大概深刻地感觉到了西海固的单调和无聊。
所以大量的镜头都用于表现自然的寂静,生活的寡淡无趣。
“生活都要苦出汁来了。
”我们在回族地区做过很长田野的师姐说:片子拍出来西海固太苦了,现实里哪里有这么苦啊。
所以影片似乎静,似乎是饱满了西海固生活的味。
但是实际上,这种几乎空白无物的静,恰恰显露了导演虽然生活了十个月,似乎并没有理解西海固人的内心。
西海固历史上是封建王朝放逐“叛乱”回民的地区,是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干旱少雨,地几乎是寸草不生。
但是这个地方的回民扎住了根,生活了下来。
他们是不同的。
这是西海固人引以为傲的一点,我们惯常思维中“人穷”与“文盲”相连的固化思维在这里是不适用的,因为门宦文化和宗教本土化知识的灌溉,西海固人物质尽管可能一无所有,精神却极其富足。
马子善老人会思考生与死,会发出“人不如牛”这样智者式的诘问——他绝不是仅仅在惋惜那头牛。
不同于我们在这纷繁世界里有那么多东西要考虑,地铁涨价了,暖气停了,堵车了…在西海固,人们赤裸地面对着人生最重大的问题:转折。
何谓生,命名,婚姻,宗教,死亡。
在牛身上,老人看见伊斯兰门宦牺牲自己的先知智者们,那样遥远的知识与现在面前的处境轰然撞击,合二为一。
他因此获得了“知”的更高境界。
而片子在努力表达自己的理解的时候,浅尝辄止。
满足于对回族仪式习俗的穿靴戴帽,大量铺张的习俗表达,大净小净,礼拜,盥洗,反而失去了对核心精神的一再强调。
《清水里的刀子》的核心,是清洁吗?
我觉得不是的。
而当影片把注意力全放在对仪式的符号性表达时,能指因为失去了笼盖在上面的“故事”而变成了所指本身,也就失去了厚度和力量。
去除这些隐喻,作为故事片的本电影,实在是太过单薄。
而作为自主主体的回族,也在这种单薄中沦落为一个个不够具象的符号。
而实际上,他们除了悲伤,沉默,也是思维活跃,会欢笑,想要追求知识和幸福的个体,他们在艰苦的西海固生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力旺盛的斗争。
这部片子里,我们只看见了生命沧桑沉淀的痕迹,没有看见那种惨烈搏斗尽情张扬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力。
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也正是当下少数民族电影普遍的一种缺陷,对于某种异质过度强化,却忘记了我们本来是同胞,是一样拥有喜怒哀乐的人。
这在声音效果上表现出来的另一个缺陷便是风声的去除。
为了与整片的静谧氛围契合,导演削减了影片里的风声,且因为对气候的执念,干旱得几年可以不落一滴水的西海固,硬生生在一个93分钟的片子里下了两场雨一场雪。
西海固地区本来是大风起的高原。
而风是什么?
风是力,是绝望的自然与不甘心的生命,有风的高原,才是苏菲的高原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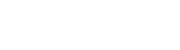







































镜头和光挺好的,朴素干净。但是真的无聊。
再次证明刻意拉长短篇就会很容易变得无聊 并不觉得导演真的多会表达 反而有一种看啊我拍得多好的气质…
镜头异常冷静地展示了日常琐碎。老爷子杨生仓的表演看着挺好,饰演儿子的演员不是专业的吧,有时眼神有些飘。
很好,评分太低了既是一种讲述,也是一种记录艺术的力量来自真实生命如此漫长,又如此短暂;如此脆弱,又如此坚韧
在影院会闷,大概文艺青年喜欢,其实演员不错,但把原著繁复化然后认为是卡佛极简,感觉好像不够成立。
只是让我了解,中国还有一个又缺水还缺粮的穷地方。咋办呐?说好的“最后的思考”在哪?
2018-141。贫穷、小众、宗教是很多“文艺”的小标签。影片拍的就像一部纪录片,缺少表达,躺在那里呻吟你要理解我,你要爱
已经够卑微了,那么更要坚强下去。
1.打光师的电影。2.人在自然之中找不到自由,因为永远会有把刀以倒影出现,我们对死亡和失去感到惋惜。3.大净小净印象深刻,很少能在国内电影里看到人以为人的尊严被如此恰当地正置。4.无形和有形之间,也许是一次交流的冒险。
SIFF2017-18 极简 4:3的画幅把整个情绪都压住了 不动声色的压抑 荒漠里的雨和布满深纹脸上的眼泪 认知死亡和信仰 昨天看了个藏传佛教的 今天就来大西北的回民了 我觉得隐藏在小县城里的基督徒也应该被关注一下…
简单纯粹朴实深刻。有些东西是故事讲不透的,只能靠画面和造型。
一部被死亡牵动的电影。导演将已死、将死、必死构成精巧的三线结构,事关生命。导演下了不少功夫,电影的构图和摄影非常有力。虽然电影非常残酷,但充满了情感的温度,还有老人的倔强和温柔。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爷爷。长镜头很考究。事实上,真正的现实无比生猛,但导演并没将诗意沦为遮羞布,也是难得。
巧妙的构图灯光,油画的质感,对塔可夫斯基和安哲的致敬,回族人清洁的精神,对生命与生死的探讨,缺一星给睡着没看到的那部分
搬演式纪录片,格里尔逊模式
或许是数码版的原因画质很糟糕;有些镜头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感觉很对,拍得也很干净和克制;倒是觉得在这种生存与信仰中故事性较弱是个很大的优点。片子到了最后也没有出现配乐,放映员大概睡着了忘记了开灯,几个人在黑暗沉默的电影院看着一行行演职人员的名字到最后,就好像我们也进入了某种仪式。
太过注重风貌也仅此而已。
BJIFF。在93min的影片中,导演涉及了生老病死四个永恒的命题,并将之安排在西海固这片荒原上。生命的无意义和企图从中找寻意义的两股力量在这片土地和生活中互相撕扯。镜头缓慢且充斥着苍凉,画面阴冷并夹杂着挥之不去的雨雾。背景音除去风沙便是钟表的滴答声。很有气质的电影
做饭和洗澡的画面风格像级了维米尔的油画。至于印象表达上,不知道导演是学习了德乐滋还是侯孝贤。
感觉是《都灵之马》+《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合体,摄影真棒,宁夏穆斯林居民日常生活的仪式感和宿命论,牛为大牲有灵性,懂得自我清洁,但是那里的居民呢,老无所依,为生活所迫,怀着对亡人的思念、老牛的愧疚等待死亡。
摄影大赛优秀作品